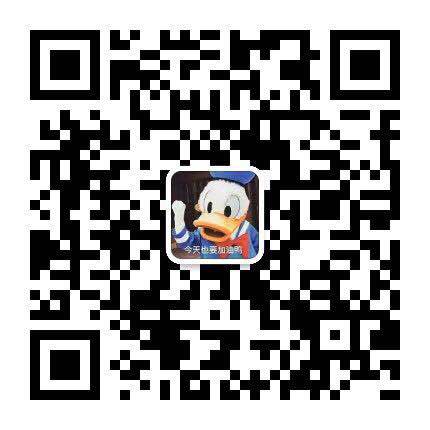摘要: 10月暮秋,留学荷兰(微博)并定居荷兰的台湾作家丘彦明从居住的圣;安哈塔小村而来,在北京逗留的几天,正是清明透彻的时节,景色绚烂,爬山虎红了,灰瓦屋顶上的秋草黄了。无论到哪儿,先吸引丘彦明的总是植物。在胡同口的咖啡馆坐定,丘彦明说起沿途所见瓦屋上的秋草在日光中闪烁的迷离光影,又莞尔低眉解…
10月暮秋,留学荷兰(微博)并定居荷兰的台湾作家丘彦明从居住的圣;安哈塔小村而来,在北京逗留的几天,正是清明透彻的时节,景色绚烂,爬山虎红了,灰瓦屋顶上的秋草黄了。无论到哪儿,先吸引丘彦明的总是植物。
在胡同口的咖啡馆坐定,丘彦明说起沿途所见瓦屋上的秋草在日光中闪烁的迷离光影,又莞尔低眉解释:跟植物在一起总是好的。午后的光从其身后的窗棂上漏下来,她穿杏色碎花衬衫领口系上酒红细丝绒蝴蝶结、小黑裙和扣襻皮鞋。一出家门就很开心,每次都像放风,东张西望。一连串闲话将琐碎心迹轻巧地串起,喜欢窜胡同,看到有趣的人就想聊天。刚走出旅馆,见一位老太太在胡同里晾被子,被子是有被里和被面的老款式,被面的图案洗得发白,暗淡馥郁的花朵,破了的地方用绣片缝补,很好看。想要拍一张绣片的照片,于是向前探问老太太可否。老太太大约心里有气,顿时恼了说:这明明是破,哪里好看了?丘彦明便忙不迭道歉,老太太一不做二不休,稀奇古怪地拉起她,到隔壁一条正在翻修的胡同,喋喋抱怨施工带来的干扰。
这是富有现实感的生活,与荷兰的闲心日子不同,无序、矛盾,每个人努力维系有限的平衡。今天的胡同也是这样的矛盾体,要么破旧不堪,看了尽是沧桑,要么修得崭新,找不到可怀念的过去。丘彦明说。
大概心思活泼的人,在途中往来行走,总会比心理受到更多束缚的人有更多机缘触碰新鲜事物,而他们口中的故事也因此有了更为绵密的机趣。丘彦明说到有一次跟朋友在乞力马扎罗山下游玩,漫坡开着白色的咖啡花丛,一位老太太端着自酿的啤酒堵在路口,央给她喝。因为这里距离朋友工作的艾滋病医院不远,加之老太太又是陌路人,丘彦明心里有所忌惮,但又不忍拂了老人的美意,想来想去便豁出去把老太太塞到跟前的啤酒喝了。
这位凭空而来的陌路老人与白色咖啡花丛的记忆场景,被丘彦明写入新近出版的《在荷兰过日子》的杂文集,这本是一部记录荷兰本土生活的图文集,却因嵌入许多类似的异地亲历与所见,而有了叙述的宽度。
真正的生活艺术
从《浮生悠悠》到后来的《荷兰牧歌》,再到眼下这本《在荷兰过日子》,丘彦明用文字、图片和素描细致记录和丈夫唐效在荷兰居住的日常生活,行文与画笔皆素朴绵密,悠然闲适,但她下笔常不忘告诫读者:这种小资的生活方式说实话似乎不值得年轻读者借镜。在她看来,每个人在自己的现实条件下,找到一种自洽,高高兴兴地过活,是真正的生活艺术。
与丈夫唐效在荷兰的生活从1990年开始,告别了之前效力十年的台湾媒体圈,过着静寂缓慢的日子,不是为了哲学思考,而是过日子,很真实地劳作会让人发现以往无视的乐趣,而生活应该是一点点小快乐就可以很满足了。她说。
在舒思特居住时,丘彦明从租种社区的居民田园开始学习种地,翻土、埋种、灌溉、施肥和治理农害,直到收割,这些劳作的场面曾是她童年生活中台南老家窗外的美丽图景,她依据记忆、想象和问询,学习农事的每一环节。2000年搬到圣;安哈塔小村后,不再耕种居民田园,而是在自家园中辟得100多平方米的花园,又在二楼晾台上种上果树,春季果树开花,一丛丛繁复、璀璨,果树长得疯狂,自己去修剪,每次剪完手臂酸痛,剪的时候很有成就感,剪完之后会后悔。丘彦明笑着说。
圣;安哈塔小村的新家,正中园子近旁是十五六平方米的温棚,栽种需要恒温养护的蔬菜,加上屋后十多平方米的菜园,自己种的菜吃不完,便送给近邻和朋友;园中车棚和储藏室之间,则用柏树围隔出一个小天井,地面铺了泥砖,养盆景。料理这些植物占满了丘彦明每一天的生活,而写作的素材也多来自每天碰到的新的问题和感想。
有勇气,则不同
朋友言及丘彦明会用勇敢来形容,仿佛人所面对的每次转折在旁人看来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事,反而当事人自己视之为自然而然、机缘如此,唯其漫忆成长往事,才能找出些心志上的缘由,佐证其后的转变。
在父亲对丘彦明的教育中,有一种明显的纵容。父亲好像从小就不希望我成为和大家一样的人。丘彦明说,上*时,大多数父母都愿意选择看管严的、功课好的学校,父亲却偏把她从好的*里转到一般般的学校,因为功课不用太紧。不但如此,还跑到学校跟老师商量:丘彦明必须九点睡觉,不用给她留太多功课。
当时很气父亲,老师也不高兴,经常当众说:丘彦明这些功课你不用做。当场羞愧极了。越是这样就越想跟别人一样,做他们一样的功课,晚上偷着做,一到九点就被父亲没收了。之后的人生确实很勇敢,不被体制约束。现在想想,当时父亲所放弃的是很需要勇气的。在过于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生活,需要个人有勇气选择不同的路。
小女孩有些精灵古怪的脾性,总是会多受眷顾。童年时的丘彦明,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儿,她有神奇的脾性来自梦境。她说:十八岁以前,我有一些奇异的本领,和梦有关。像一个沾染了鲜灵露水气息的小说开端,丘彦明话头一转,从田园生活说到奇异的梦境。
有三个梦一直记得:*三年级,有一回梦到骑单车,醒来对自己会骑车这事深信不疑,下楼推起妈妈的单车冲到学校运动场,想都不想就骑上去,没有跌倒,仿佛梦里得到的能力在现实延续;还有一回做梦考数学,梦里埋头很舒畅地写,第二天的卷子竟然如同梦中所见,很流利地答完;再有一回,梦到会有人来送两瓶红酒,清晨醒来对家里人宣布了这个梦。临近黄昏,送酒的人没来,妈妈笑她这回失灵了。不料天将黑的时候,父亲的同乡一位老伯,送来了酒。
但这些奇特的梦的灵性,过了十八岁就失去了,而她却一直相信冥冥中有不可破解的神秘的存在,比如,哪天运气好,文章就写得顺畅,哪天运气不好,即便想好的,确凿以为可以写得很好的文章,后却写废掉,很是怅然无味。
永远解决近的问题
顺乎天性地生活、永远在解决离我近的问题,是丘彦明从自己的经验中找得出的两种心得。以每天的生活为例,丘彦明不会比丈夫更早起,好为他勤劳地准备早餐。她以为,醒来的时候自己需要一段独立的时间,考虑考虑一天的打算,想必唐效也是如此需要的,所以不会起身打扰。等丈夫出门上班后,才到园子里,先看到哪株植物有问题,就立刻解决它的问题,常常忙完,已过正午。
家住小村,就有许多务农的朋友,大多是爽性的人,交往简单、愉快。过去在舒思特种地,惬意的时光莫过于到隔壁农地里跟主人罗伯喝杯田头的咖啡,如今搬远了,一年收到一张罗伯的明信片,澹泊而温暖;农妇衣饰总是很艳丽,叫人看了觉着喜兴,可能是因为荷兰的天很低,天与地的距离很窄,人们希望用鲜艳的东西把这个空间撑开。丘彦明相信,不同的自然条件融入于人心不一样的苦难意识,并决定了人们获取快乐的方式。过于漫长的荷兰冬夜,赋予人们编织灵巧的黑色笑话的能力,而荷兰的民间故事,总有很多非常血腥的场面,荷兰人却不以为吓人,似乎是因为黑夜压下来太重了,当整个穹窿笼罩下来的时候,跟更大的自然力量相比,人间的杀戮于是显得很轻微。
看惯了荷兰电影里沉重的故事,回到台湾看台剧就完全不能适应。台剧太容易让人流泪了,而荷兰的故事总是很沉重,所有的难受全压在心里,眼泪根本掉不下来。在这样一种气氛中生活,容易让人觉得在人世生活真好,一点点小快乐就很满足,反而是那些易于流泪的故事,让人的心肠变硬。丘彦明说。
其他资讯:三分钟知晓赴美留学体检流程
其他资讯:托福口语备考盲点分析
其他资讯:河北*生澳洲留学的条件
其他资讯:美国经济学专业申请文书包括三项